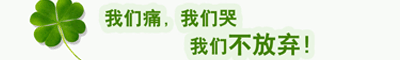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像前代经师那样不恰当地断定诗中的“比”,造出了《诗经》中所谓“诗人之意”,歪曲了文学作品的内容。
3.在“赋、比、兴”中,最烦最难的是“兴”。它之所以烦、难,是因为它的意义空洞,所以讲“兴”的人也就随意发挥。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是“有感之词”。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朱熹则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把所有解释“兴”的词抄列在一起,也难找出一个共同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不少阐释《诗经》者,凡要将诗列入政治教化的内容,便称此诗为“兴”的手法。 “兴”有启发之意,但如果解释过于穿凿,便歪曲了诗的原意。《卫风。淇奥》就是用“兴”的写法,全诗三章,诗每一章的开头分别是“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都是诗人所见。所见在此,所得在彼,引起了对卫武公的颂扬。但前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必然联系。这种手法使诗文收到情景相映的效果,以景补情,以情托景,于斯为胜。《诗经》中还有不少以“采”为“兴”的诗,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周南。卷耳》)、“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周南。芣苢》)、“爰采唐矣,沫之乡矣”(《鄘风。桑中》)、“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王风。采葛》)等等,古人对这些“兴”的看法不同,有说之为比,有说之为赋,但大多数人同意其为兴。 对《诗经》中“赋、比、兴”的看法历来都有分歧,但又常常强调诗歌中的比兴作用。在今天仍是重要的,特别把这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经》中对文学语言这门艺术的运用,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凡今天的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大多运用完美,像比喻、借代、夸张、比拟、对偶、对比、排比、衬托等等,例子举手可得。这些手法的运用,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完美的艺术境界。 最后我们谈点《诗经》中的意境。如《陈风。月出》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在阅读的时间流中,人们从声韵之间,便会体会到意境的广阔与优美。诗共三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诗中形容月色是皎、皓、照,形容容貌是僚(美好)、■(妖媚)、燎(漂亮),形容体态是窈纠(苗条)、忧受(徐缓婀娜)、夭绍(轻盈)。 天上有皎皎之月,月夜之中有娇娇之美人,诗中的“窈纠、忧受、夭绍”又是声韵母相同的字,读起来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感受,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畅,只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感觉,正是诗朦胧的意境所提供的。《秦风。蒹葭》则是运用暗喻、象征的手段,寓情于景,寓理于情,把人引入一个迷离恍惚的境界。诗共三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是写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爱人的追求与景慕。诗以一片白色的秋水和清霜白露为背景。这背景本身就不一般:清寒而纯洁。在这白色之中,优雅闲静的佳人,或在水中央,或在水边草地上,或在沙洲之上,这种跳跃式的描写,仿佛电影一样。这样写,更能衬托出佳人可望而不可即,追求者始终在崎岖而漫长的道路上。这条路正是生活中爱情之路,道路迷茫而感情执著。 整首诗景、情、人都是美的,艺术境界也是美的;而读者品尝到的,却是甜而苦涩的爱之真谛。这一类诗,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宋词影响非浅,在此不一一举例。 《诗经》的艺术手法,像潺潺的清泉,滋润着无数诗人的心田。从《诗经》—楚辞—陶潜诗—唐宋诗词—当代文艺,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曲折而明晰的线索,看到中国诗歌的借鉴、继承和发展。 在分析《诗经》时,我们仍然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正确看待诗中的精华和糟粕。如《大雅。云汉》等一类诗,写人民遭旱仰天,充满了鬼神活动。但把这简单地斥为糟粕,是不合适的。因为神奇的童话,正是先民对自然界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人类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不可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想象是幼稚的,却又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对这些作品,我们应当从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去研究,并给以适当的评价。 |
|
相关文章推荐:
|
- 上一篇:亮煌煌开创新纪元——《新民主主义论》
- 下一篇:九曲回肠泪洒丰碑——《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