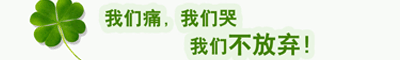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
女性散文的文体自觉意识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自觉意识并没有作为传统深入到所有女性写作之中。对于很多女作家来说,散文创作往往是小说或诗歌之外的一种附属品,它承接的只是过剩的热情,或是热情消退后的无奈,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往往被忽视。
从凭借先天的良好的艺术感觉而从事于写作,到认识到文体的独立性与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突破规范的途径,从而重新进入到自由之境,这是散文在否定——肯定——否定的辨证思维下的重新整合,也是散文家进入到创作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的环节。对于散文来说,恰恰是在坚持某种规范的情况下的“反规范”,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创新。
当代散文家对于文体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缺乏认识,散文的纵向演变与横向比较,以及文体的历史意识与宏观意识都显得匮乏,而这也便直接导致了女性散文的视域比较狭窄。事实上就汉语散文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汉语散文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以汉语作为散文写作语言的诸多群体,包括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诸多华人居住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等等,这形成了汉语散文在二十世纪后期“多元发展、共生互补的繁荣鼎盛的整体格局,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就世界散文来说,它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概念,很显然散文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在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不同的文体形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散文的比较研究将会变得艰难。但是即使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五四”时期中国散文建立的开放性的传统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薄弱。现代散文在开端时便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姿态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和世纪初的很多个年头一样,2006年的文坛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喧哗无非是来自图书市场炒作的名家或80后,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奇怪的“诗歌”,以及文学官方机构权力的更替,这个时代能够沉淀下来的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百年后人们书写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大概会吝啬到不落一字吧。
新生代的作家既有力图突破以往散文模式的“新散文”作家,也有一些都市休闲散文的写作者。这是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女性散文领域的两种创作潮流。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新生代的女性散文家以及创作流派的出现,再加上已有的老生代、中生代的女性散文家,女性散文真正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是不断的向生命的深层空间拓展,一方面则是开始与市场的快餐文化妥协。一方面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冲击中国女性的写作,另一方面传统生活以及古典文化依然是中国女性散文挖掘不尽的话语储备。老生代散文续接着汉语传统中最为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作家则开始了新潮散文与“新散文”的实验。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很多词汇都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分裂运动”,我们在将某些概念简单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将很多词汇复杂化,就像对于“爱人”的分解一样。“妻子”与“爱人”已经分离,在欲望化的体验之中,名分与内涵,现象与本质都将回到自身,并生成新的外延。所有的事情都在疯狂地朝向某种不可预测的方向转变,神圣的将变成荒谬的,真实的就要变成历史记忆。让“妻子”与“爱人”合而为一成为一种理想。
在今天,我们的阅读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的沉淀。事情发生了——疼痛和死亡,执着与背弃,然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又隐藏在哪里呢?
文体,又称文类,文学体裁或体式。在这里不是指文学的叙事和修辞意义上的方式。文学体裁的划分方法依据传统分类法,可分为四大文体,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每一个时代关于文体的选择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拒绝了小说,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形式,而明清时期却是小说的辉煌期。我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时期某种文体的创作成就的指认,也是对一个民族的审美形式和文化精神的概括。
如果回溯中国文言散文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散文正是中国文言文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钦定文体。文言文在日常话语之外又构造出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是将多数人排除在受众之外的。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汉语散文应该成为东方审美传统与西方现代精神的一种结合体,当然这首先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散文家自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种结合。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本身对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具有间离意识,她作为文化的客体并没有阐释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散文作者更容易形成某种开放意识。事实上,中国女性散文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借鉴,新潮散文对于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都使我们看到女性散文的巨大的创造性与可能有的开阔的视野。
建国后,我们一直将普通话视为一种标准的书面语形式,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语言有着更为丰富的资源与支脉。如果没有方言、文言与口语等语体形式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支援力量,那么普通话将是语言等级秩序中的霸权者,白话将失去汉语文化传统的根脉之一,而书面语将只能是呆文,汉语文学语言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而语言一旦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存在价值,便也就失去了它自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它能够提供给人的想像力也将受到限制。语言的荒漠往往就预示着我们自身的匮乏。
“五四”以后,文言散文的传统被中断,而文言作为一种语体形式也成为汉语语言的过去时。语言的灭亡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随着时间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语言自身不断发生变化;一种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从而人为地中断语言的某种传统。“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传统的中断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就“新散文”试验来说,文言文化中可能会继续保有生命力的因素应该成为新语体的内在滋养,否则散文创新的基础便会显得脆弱。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散文在语言形式以及汉语文化的继承方面比大陆散文更多了与传统的渊源关系。
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仍然在文言与白话间寻找某种“化”的可能,“化”是在形式变异下的对于原话语的一种潜在的转义行为。冰心就曾经主张语言要能“化”,即“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并认为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但是这种“化”的转义在随着白话文日渐成熟、民间语体的不断深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语言大众化的要求等等情况下,逐渐失去它的转换的可能。
汉语言自身的灵活,骈散相间,参差错落,仪态万方的美质并不是汉语与现代性接轨的不利因素,相反,它是这种现代转向的基础。当下的散文语言过于注重语言的标准化、书面化,往往只是由书本到书本地转化某种叙述方式。而另一方面网络写作又过分注重外来语汇以及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的时尚词语和完全情绪化的感叹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事写作,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写作对于官能感受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审美感受。现代人越来越复杂的心理体验在无节制的宣泄中变得苍白,网络写作包括网络散文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们无法对“母亲”进行福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一种简略的办法,是通过传统文化下已有的母亲类型来透视母亲概念的生成过程。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史之前的母亲形象,包括民间戏曲、文学文本以及口头传说中的相关资料作为参照,以切入这一主题研究。——王虹艳语录
贤妻良母型。这是男性书写中关于完美母亲形象的最普遍的典型,它不仅寄予男性期待视野中对母亲形象的理想,同时也是对一个完整家庭结构中女性角色的设置——贤妻良母本身就已经暗示了父与子的在场。而与妻子、母亲的贤良对应的正是父亲与儿子的权威。
中国传统文化秉持一种以和谐为基本原则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观念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对于女人而言,这里的“天”与自然意义上的“天”,或者说与人生境界中的“天”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天”直接指向的是父、夫、子。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旦进入日常语境,一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人便不仅仅只是认同或迎合传统文化赋予她的角色界定,她更进一步地同化在父权意志的威严中,并在主流秩序的边缘处仿构出女性亚社会秩序的摹本——它建立在对更年轻的女性生命力的框正与压制上。这就意味着女性在亚社会文化中摹仿的正是主流文化等级制度及父权至上的家庭戒律,这样母亲在服从、趋附之外,现在她又增加了“执行者”这一隐性身份,而这正是贤妻良母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大量的悼亡诗、忆内诗、寄内诗都记述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的功德,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等将母亲教育与子女成才直接联系起来,直到今天贤妻良母仍旧是男性视角中女人的主要价值。当然“五四”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启迪了新文学的作家们将母亲与个人赎救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
中国封建文化的贞操观念为一个母亲尤其是寡母设置了唯一的可亲密的对象只是儿子,爱子就等同于爱亡夫、爱公婆。但是,一个将女性推向“恋子心理”的畸形规制,却反过来禁止并讽刺女性趋向这种心态。
贞烈观落实到对“母亲”的定义时,很容易被置换成自我牺牲、奉献等。如果说,以往“牺牲情结”对于母亲来说只是一种基于母爱精神之上的本能,那么现在,它通过伦理灌输已经成为一个母亲的显意识。也就是说,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被归纳为一种伦理学模式,这种模式将女性的母爱天性演化为一种自觉的无条件的责任感。
当牺牲与奉献成为母爱的代名词时,“成为母亲”首先便是对于一种母者精神的信仰。是的,从身体的疼痛到精神的凤凰涅盘,最后在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激情中执迷,母者认同了她作为社会规诫对象的身份属性。也正是在这里,母者把自己供奉在父性的神坛上,她不得不等待一场新文化下的解放和复原。
学界不断出现关于一些概念的讨论,其实说到最后,也往往难有定论,尤其是近期内的“纯文学”“文学性”以及“好作品”等等,不仅不可能有定论,也不宜有定论,因为很多所谓定论式的东西往往会带来单向度的实践,就像“底层写作”近几年内频频亮相,它由作者的自发的写作,变成评论者理念上的总结和号召,然后又回到作者那里成为自觉的响应,现在变成了一窝蜂式的跟风和雷同。
反对以“纯文学”来界定文学本体性的人,很多是因为他们认为纯文学的概念偏重于形式试验,偏离于现实批判,拘泥在主体内心世界中,是典型的“内向化”的写作。而我认为纯文学和主题、题材、写作风格、艺术追求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你不能说某篇小说进行了文体试验就一定是纯文学,也不能说某篇小说写了贫困的底层就不是纯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审美的超越性——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超越历史和当下,最终信靠在美神指引的方向上。
当然,纯文学势必是小众的,它在特定时期可能不被认同,它是少数人为之殚思竭虑的艺术创作,是具有崇高感的文学朝圣。在它所开辟的文学疆域中,矗立着几乎所有文学史上的殿堂级人物。
当然更多的文学期刊仍然希望在艺术与可读性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让杂志活下去,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作为纯文学期刊的尊严。可以说对于很多文学期刊,文学仍然是一种和灵魂相关的神圣事业。
强调“崇高感”或者“神圣感”这样的词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后现代哲学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让大家认识到了文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文学能够承担的责任其实很少,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很少,作家不应该把自己太当回事,传统的所谓深度、责任、神圣感都是可疑的。
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建构的时候:重新想想纯文学的事情,即使我们并不能严格的定义或者划分;也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回到爱与美与自由的旗帜之下,拣拾起我们一度嘲笑的那些使命感或者神圣感,让写作听命于内心世界,而不是随声附和或者跟风从众。在一个浑浊蒙蔽的时代重新做一个作家,重新回到文学的神圣的殿堂。
二十世纪的散文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散文文体的范畴论、特征论等等都在很长时间内引起评论界的争论。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散文的日渐走红,散文批评更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而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散文理论的每一点共识都伴随着争论和媒体的炒作,这种争论本身使九十年代的散文研究呈现出既浮躁化又多元化的特点。
八十年代的散文批评,主要是集中在对于现代文学中散文理论的整理,以及对现代散文史及散文艺术论等方面的关注。但是更有意义的是这一时期对于17年散文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这直接影响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与理论的发展。对17年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杨朔模式”、“形散而神不散”、“轻骑兵论”、“海阔天空论”等一些权威性观点的批判。
关于“新散文”,批评界始终都是以一种极大的热情来鼓励召唤它,在八十年代,几乎每一种文体——小说也好,戏剧也好、诗歌也好,都开始了“探索”、“实验”、“先锋”、“崛起”的过程,但是唯独散文的园地静悄悄,似无人耕种一样。面对这种沉默,散文理论家开始积极呼唤具有现代意识的散文的诞生。
在文体的规范方面,“大散文”与“文体净化”互相对立。八十年代,林非的散文“广义狭义说”,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广义散文包括了抒情、议论、叙事等不同特质的散文,而狭义散文则是以抒情为主的散文,当然也并不排除智性的思考。——王虹艳语录
|
|
相关文章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