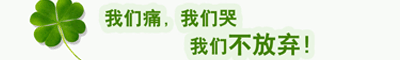这是近几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底层写作”是关于底层的书写,而不是底层人自己的写作,它与一度非常热闹的“女性写作”的概念方式恰好相反。现阶段“底层写作”虽然不能构成大规模的创作思潮,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种创作现象。
作家的视野突然聚焦到底层,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状带来的启示,大量的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农民,迅速从社会阶层中剥离开聚合成一个浩大的弱势群体,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比,这一群体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其面临的境遇也越来越残酷,就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社会以及文化现象很容易便演化成文学现象,更何况很多作者的经济状况就在“类底层”之中,他们关于底层的叙述其实也是关于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
关于底层的叙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矛盾的简单化,把底层人的悲惨境遇简单地归结为村长或者包工头的腐败或剥削,并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划上了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
底层写作触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问题并不是全部,作者以怎样的想像力和叙述方式将问题带入文学的层面,从而通过具象而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现实以及审美的启示,这个是重要的。而当前的底层文学欠缺的不仅仅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有艺术上的表现力问题,而这也恰恰决定了底层文学能够走多远。
虽然我们不会完全认同于“文学是历史的书记员”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文学反映当下中国人的婚恋状态时,它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书记员。整整一年的作品读下来,没有婚外情、离婚、偷情这些素材的小说实在不多,区别在于有的小说在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有的则不再质问,而直接把这些元素当成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来在文学中与同性恋有关的题材逐渐多了起来,同性恋或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内容或作为小说的一个元素,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切入了我们并不了解的生命以及爱情的陌生地带。
同性恋作为少数人的真理很容易令人想到现代以来一切“少数派”的权力运动,如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等等,因而它也天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学表述对象,但是真正的同性恋文学应该不是事件层面或发生层面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存在层面的同性恋——作为人类存在之一种,它以怎样的方式唤起我们关于爱与自由的想像。
相较于热闹的图书出版市场和网络文学,文学期刊毫无疑问是寂寞的。每一年多数的文学畅销作品由出版社走向读者,而由学期刊发表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数都自生自灭,或者只是在一个小众的圈子产生影响;人们更多记得的可能是某网站关于年度作家或作品的的评选,每一年各大期刊的评奖活动最后不过是报纸边角处的短消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少之又少。
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驳杂的时代,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阅读是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先锋派们沉重的诗性意识与颠覆性,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承诺后,变得苍白可笑,最终走入绝地——一个大众文化勃兴的时代从本质上拒绝先锋,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先锋。
在散文回归内心、回归自我时,女性散文家们也同样开始了面向自我灵魂的书写。这一时期女性散文的代际现象较为明显,老生代如冰心、杨绛等的作品更加炉火纯青。尤其是杨绛的创作更是显出深厚的艺术修养。
杨绛的散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西方文化素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她的散文既有丰盈的文气,淡定的气质,同时也有较广博的学识,能够在平和中见锋芒,不动声色中见惊心动魄。在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散文界,杨绛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多篇作品都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中的经典。
八十年代早期,当人们还沉浸在回忆伤痕与反思历史的时候,曹明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在”的叙述。十七年的“革命叙事”,文革后的“伤痕叙事”,在这里都被“个人叙事”取代。“个体”作为一种日常情境下而不是特殊使命下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出来,理想与主义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游历。——王虹艳语录
每一个大都市里都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繁华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异乡人的世界里。她们用整个生命哭泣与微笑,拼尽全力扞卫自己幻想的权力,拒绝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担她们的幻想,却从来没有成全过她们。而在暗夜的狂想里,城市逐渐成为心上的一道伤口。她们深陷于一种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乡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纷乱的城市里唯一永恒的传奇便是爱情,但是爱情已经蜕化成文字域里的一种想象。正是在这里,我想我能够明白安妮宝贝们对于文字的执迷——每一次写作都是与幻觉最近的时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宝贝们将虚构视为一种救赎。
对于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写作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她们可以将写作视为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文学她们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说到底,写作只是一种行为,而文学则意味着创造。写作某种意义上只是小资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类,意味着不同凡响,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我们只是一个观望者——站在审美的立场,最后悲悯于一切的无常,我们并不知道救赎之路到底在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审美主义者也许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如果我们翻开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的作品,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晰的:在大多数女性文本中,母亲与爱情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关于母亲,她既是女儿的守护者又是她们的对立面。
在普遍的抒情化、简单化的时代,张洁依然力图在叙事的辉煌帷幕中开启她晚年的一部大戏,细节性的再现,哲理性话语的彰显,人们久已疏忽的或是不愿再去经营的典型与细节,终于被大气的张洁拨乱反正,《无字》在延续作者以往作品的精髓上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它却并未开辟出更多的话语空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散文是记载正史的方式,也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学”“仕”一体的思维方式。文言散文的世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权力化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恰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她被告诫要远离她的话语权。很显然女性不可能真正进入到一种排斥她、塑造她的文体创作中,她已经被先验的排斥在正史之外,她的创造性是被怀疑的,尽管这种怀疑并没有原因也没有经过证明。
散文在父权世界中所具有的主流性的话语功能正与女性的边缘地位、边缘情感相背,性别之“轻微”与文体之“凝重”形成鲜明对比,文言散文拒绝女性话语的介入。
直到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言文一体”使文学的大众化有了讨论的可能。白话文学要以国民意识、写实精神、社会性代替了以往文学的贵族气、古典做派以及山林气。语言与生活的同构,王纲解钮时代的混乱与缝隙间的自由,英法随笔的引介,文化先锋们的素养,使得白话散文在发轫期便迎来了高潮期。
从都市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存在状态与写作状态,它没有修饰,更接近多数女性生活的日常状态,也更细致的勾画了女性世俗生活的图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平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企图超越平庸的愿望——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在斤斤计较的现实牵绊下,梦想着“别处的生活”。
追随梦想的声音使女性散文呈现出一种先锋姿态和创造意识。女性散文是女性存在的审美见证,是关于女性生存的诗意言说。审美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中的生活。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女性的新潮散文在文体形式上有了试验的性质。斯妤很多散文开始表现女性的潜意识结构。事实上人类心灵的深度空间以前一直是小说的领域,散文表现的更多的是人的显意识,而不是难以捉摸的潜意识。
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现在的“新散文”则展现了一种“戏剧化的自我”。如果说以往的散文更注重“我在说”,那么新散文则是“在说我”,我是被表述的对象,是具有戏剧化特征的被塑造的自我。
凡此种种,当散文成为女性凝视人生世界的一种方式,当散文承载女性对于一种理想世界、理想生活的期盼时,我们发现文体的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与女性自身的敏感与唯美气质结合,女性回到自身,回到世俗生活的平凡琐碎,也回到心灵世界的伟大的戏剧性中。
散文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女性生存方式与言说形式的合而为一。散文的日常性使她成为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很多老生代的作家来说,散文成为对抗宿命的一种方式,它与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所倡导的审美核心——意境——无关,它甚至与审美本身也没有关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生存记录。这是我们在女性文本中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存在方式。
新时期后,有很多“五四”以及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的作家,这时候因为年龄或者运动中的摧残等等,她们的身体以及创作力都处于一种衰弱的状态,但是她们仍然在创作,此时写作仅仅只是一种姿态,是向某一种势力或者是生命力本身的宣战,这时候,被她们广泛采用的散文文体,严格的说并不是一种文学体式,而是一种生命形式,文学性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凸现在文本中的是个体生命在劫难后向自我的一次“交代”——就像文革中她们向“组织”交代,现在她们向自己交代。
文学的审美意义被一种纯净的表达的欲望取代,散文在它的最高意义上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生命,它不需要华丽的文藻,不需要运筹和方式,不需要想象力的驰骋,生命本身的激情成就了一切。
汉语散文新思维有着多种层面的所指,它首先应该是针对文体本身的认识。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凸现文体本身的美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以一种实验创新的态度面对散文。其次,是汉语散文的宏观认识。这是把散文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是在汉语写作内部,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之中,给汉语散文过去、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定位与瞻望。
每一种文体本身都有它独特的审美品质,建立文体意识首先应该认识到文体的这种独特性,任何关于文体的实验都是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将它抹杀。散文也是这样。它自身的种种特质既是对创作的限制,同时也是它的优势。——王虹艳语录
|
|
相关文章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