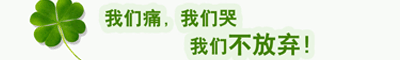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
最慈爱的父亲
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据母亲说,我出生后,她问父亲给我取什么名,父亲拿过一本字典,闭上眼睛任意一翻,又在那一页上任意一指,然后睁眼看到了平日少见的“笃”字,于是父亲说:“就叫笃笃!”这名字我一直用至考大学。用比较生僻的字取名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因其通俗上口而容易被老师提问。
父亲幽默诙谐开朗的性格,我觉得在与我相处时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他曾给我取绰号“小狗”。他说,因为你属狗,有许多“狗性”。其实我明白,他喜欢狗,养狗、玩狗是他业余最大的乐趣。他给我取“小狗”是昵称,是对我的真心实意的爱。为此,我很高兴。我初中时学的是俄语。一天,我在家练习“P”的发音时,脑后的两把短短小刷子随着“P”“P”一翘一翘,父亲说这非常像小狗的两只耳朵。从此,我这“小狗”的名字就叫开了。
父亲肥硕、大腹便便,睡房又在阳光充足的楼上,他登楼梯略显困难,每次登楼前都大叫:“小狗!”(意即:快来呀,我要上楼了)然后转身面向楼梯,将左手搭在楼梯扶手上。我听到喊声会马上站到父亲身后,把双手置于父亲后腰部位用力向上推。我知道,父亲并非真的困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借机享受女儿的爱,也享受对女儿深爱的快乐。
父亲对我的学业很严肃认真,但这种严肃认真常以并不严肃认真表现出来。
1965年夏,我把报考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我爱好文学,从小学到高中,在作文、语文、外语课堂上常受表扬,我总是神采飞扬,充满自信;在数学、物理、化学课堂上,我则判若两人。我那时最崇拜白衣战士,觉得白大褂、手术刀又潇洒又神秘,故在“志愿表”上填了“医学院”、“医科大学”等等,连一向喜爱的文学都暂且不顾了。父亲大逞“霸道”,撕了我的“志愿表”,又另外清一色地替我写上了一大串外语院校,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等等,真叫我傻了眼。父亲对我说:“学医是不错,有个女儿学医多方便!可学医太累,还要值夜班什么的,学外语可就轻松多了。对吧?”他说这话时不停地冲我眨眼睛,我一时不知他的真意。后来,我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录取通知,专业是日语。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这倒不是由于我出生在日本,希望女儿精通日语,而是因为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需要有人做工作,我希望有个女儿接班。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困难不少,比医生值夜班也许更累。”“噢——!”我明白了。我就这样别无选择地学了日语。
记得我第一次从北大回家,虽懂日语却因久不使用而淡忘了的祖母笑呵呵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惟一记得的日语:“你吃早饭了吗?”可惜我那时还听不懂这么长的句子,一个劲地摇头傻笑。见到父亲后,我十分得意地说了一句日语:“这是爸爸,那是妈妈。”谁知父亲听后,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好不开心。原来,我把日语中用于物品的代词“这”错用于人,这句话就成了:“这(东西)是爸爸,那(东西)是妈妈。”
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为父亲做翻译,面对许多德高望重(如孙平化叔叔)、精通日语(如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译员的王效贤、林丽韫)的资深前辈,初涉外交场合的我紧张至极。父亲站在闪闪发亮的麦克风前处之泰然,我却由于双腿颤抖,手里的译稿上下不停地颤动。虽然头天晚上我开了一个夜车译好并已很熟悉父亲要讲的欢迎词,但不知为什么,这时从麦克风中传出的我的声音却完全走了调。此刻,我体会到许多日语译员对我说过的“给你爸爸做翻译是最难的”这句话了:父亲在日本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日语不但流利纯正,而且许多典故、笑话,常令译员茫然咋舌。我看到父亲朝我瞥来的狡黠目光。他瞅个空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别害怕,你就照你准备的翻译。除了讲稿,我保证一个字也不多说。”译完下来,我浑身已是大汗淋漓。
尽管父亲平时常常讥笑我只是“小学生日语”(我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大学生,真正上专业课只有7个月),但我深知到了紧要关头,能救我燃眉之急的一定是父亲。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使我很自然地对父亲产生了一种亲情之外的类似报恩的情感以及师徒之情。这是我永生不忘的。
使我永不能忘记的还有父亲对我深爱的快乐和爱怜。记得在我读高中时,一次因面临物理大考,急得晕头转向,吃睡无心。夜深了,家人都早已去梦国神游,各种声调和有节奏的鼾声此起彼伏,想到惟有自己还在灯下受此煎熬,不免咬牙切齿。
这时房门“呀”地开了,父亲胖大的身影出现于眼前,想是夜读久了,出来走走。我抬头看他,竟然是一脸的幸灾乐祸,仿佛在说:“哈哈!这下可好了,看你怎么办?”
我大嗔,起身用力将他向外推:“快回去,快回去吧你!”他却越发开心起来,索性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撑腮作愉快至极状,一心一意要“看你怎么办”。气得我把头埋在书本中,不再理他。他却随手抢去我的铅笔,一阵的“刷刷刷刷”,然后掷过一张纸来,抚掌大笑而去。
那是一张速写,画上的我愁眉苦脸。一对狗耳朵(因为属狗,父亲喜以“小狗”称我)上架着晶莹发亮的眼镜,面前的课本上打满了问号。上面还配有打油诗一首,记得开头四句是:“廖家有女初长成,物理临考真心焦;两鬓莹莹挂眼镜,娇声狺狺摆细腰……”这张速写我曾保存很久,但后来却在“文革”中散失。而今,那半首打油诗,当然也永难再续了。
1969年春,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发配”青海,离京前“获准”去向关在“监管地”、不能回家已有数年的父亲辞行。父亲在得知我的“发配”后未作一语,但当分别时,我却看到他的眼圈已经湿润了。我一步一回头地望他,只见他的苍苍白发在晚风中拂动,直到暮色中的身影模糊难辨,他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后来,父亲把当时的心境,融成了一首《浣溪沙·遥赠》:“早起微明独对窗,秋风拂面映朝阳,腮边湿处倍清凉。昨夜无眠空辗转,几番悄自启衣箱,去年小影笑容双。”
不知何故,这首词父亲并未寄我,而只是题写在一张与我合影的照片背后。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当我看到在他那只随身携带的淡绿色的皮夹内,仔仔细细收藏着这张照片,而一经翻转,突见此词的时候,热泪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
1988年,赵朴初伯伯在读了父亲的全部诗稿后,曾经发出了“至性至情”的感叹,并且还作了一首长诗,其诗曰:“廖公殁五年,笑容时入梦。漫画多滑稽,妙语一堂哄。豪情溢四海,热忱感万众。作诗不示人,婉恋恩意重。外现长欢欣,内蕴多伤痛。知公殊未尽,能放而善控。终身慕慈母,寸草和泪供。幽居忆老妻,婵娟千里共。遥怜小儿女,题照念雏凤。生死别友朋,肝肠酬一恸。感慨读遗篇,疑云初破冻。平生饱艰危,所欠胸穿洞。动心忍性事,一一深藏瓮。出门春风扬,开户哀弦动。哀弦只自听,孤怀绝迎送。斯人有斯文,莫谓闲吟弄。”
诗中“遥怜小儿女,题照念雏凤”,说的就是上面那首《浣溪沙》。当慈祥的赵伯伯轻轻舒开宣纸,给我看他亲手书写的这首五言长诗时,开头“廖公殁五年,笑容时入梦”,就令我大恸。伤父之情,竟无法自已。赵伯伯摸摸我的头顶,亦无言。从这万箭穿心的哀恸与深沉的默然中,我确切知道,父亲实实在在是已经远走,永不能回来了……
来源《海内与海外》月刊2005年第3期作者:廖茗 |
|
相关文章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