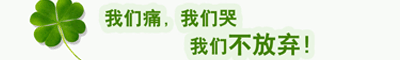作者:沈容(北京)
廖公(承志)是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使他从小就和革命联在一起。他生于日本,曾在德国、荷兰、前苏联等地生活、工作、学习过多年,懂几国文字。
我曾两度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他是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最没有架子、最有人情味、最令人敬佩和难忘的人。
初见廖公
我第一次见到廖公是在1946年1月22日,廖公刚从监牢中出来。1942年日寇占领香港,廖公组织众多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撤回大陆以后,自己却于5月在粤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6年国共和谈,我党一再要求释放政治犯。刘邓大军在平汉战役中俘虏了国民党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就以这些将领交换了廖公和叶挺将军。
我那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当翻译,办公地点在上清寺。那一天,周恩来同志去接廖公,我们外事组的几个工作人员和邓颖超一同在门口等候。当汽车到达,廖公和周恩来刚跨出汽车,踏上台阶,邓颖超马上跑上前去,和廖公抱头哭泣,我们也禁不住眼泪直流。这时的廖公消瘦、憔悴、头发很长、胡子拉碴,只是两只眼睛炯炯有光,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这是他第六次坐牢,现在受难的亲人回来了。大家把他拥进会议室里,围着他、看着他,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只有那酸苦和欢乐至今留在心间。让他休息了一会儿,周恩来就把他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了。
多次被捕,带着手铐走完长征
廖公正式坐牢,头四次是在外国,三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这六次坐牢名实相符,所以我称之为正式的坐牢。还有一次无以名之,因为除了“坐”之外,还被绑着两只手随同行军,而且没有经过宣判的手续,又随时可以被枪毙,姑且称之为非正式的坐牢吧。这是在最后一次被国民党投入监牢之前的1935年,廖公被张国焘抓了起来,张国焘杀了很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廖承志是大知识分子,还留过洋,只因他会画画,可以画宣传画,所以暂时寄下他的脑袋,押着他参加长征。那次因周恩来的努力而幸免于难,才有最后这一次正式坐牢。
被国民党逮捕的两次,第一次是1933年3月在上海。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和陈赓关在一起。因在英租界,提问他的都是英国特务。陈赓给他出主意,叫他设法通知他母亲。怎样通知他母亲呢?廖公对特务说,跟我走,特务问了去哪里,廖公说,相信我就跟我走,不相信就算了。特务以为带他们去抓人,用两辆汽车,七八个人押着带了手铐的廖公上车,廖公指着向左向右转了一阵,把特务们带到了他母亲家。何香凝看见儿子带着手铐,知道出事了。这一下,真是事情闹大了,何香凝、柳亚子,甚至孙夫人宋庆龄等等头面人物都出动营救,使廖公终于逃脱了牢宠。
廖公最后一次的囹圄生涯,先在粤北,1945年被转到重庆渣滓洞的白公馆,这是关要犯的地方。廖公在这里度过了1945年的元旦和春节。这一年夏末,特务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由特务头子毛人凤把他带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用很多花言巧语企图说服廖公投降,都被廖公顶回去了。于是,廖公又被送回渣滓洞。小说《红岩》就是以国民党特务这个杀人魔窟为背景。从那里生还的人,寥寥无几。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一家和其他几位坚持抗日反蒋的着名人物都在那里被杀。廖公能够从那里获释,真可谓死里逃生。
一人包办多种外文
1947年,我从晋冀鲁豫前线调到新华社总社。廖公是社长。那时总社已从延安撤退到涉县的陈家峪,后又搬到河北平山县的东柏坡,距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约7里地。
廖公是新华社的元老之一。新华社的前身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于1931年,由向仲华负责。1936年冬,廖公到达保安,红中社只有他们两个人。所有外国通信社的电讯由外文翻译成中文,通通由廖公包了,如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等等;向仲华负责苏区的消息。
我在总社时在外文部当翻译。我们外文部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工作,晚饭后还得干一阵。我们虽然翻译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塔斯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但只翻译英文,而在红中社时,廖公一个人要翻译多种外文!
生性诙谐,不摆架子
1978年,成立港澳办公室,属国务院,廖公兼管侨办和港澳办。我被调至港澳办,又一次在廖公领导下工作。
廖公为人随和,和蔼可亲,从不摆领导人的架子,且才华横溢、豪气干云、风趣幽默。他关心人,逗人笑,使人愿意接近他,向他谈心里话。
在新华社,他常常拍一下这人的肩膀,摸一下那人的脑袋,还爱给人起绰号。有一位广东籍的同志,他叫他小广东,我至今不记得这位同志的大名,只知道他叫小广东。廖公叫我小姑娘,时隔二十多年,我到港澳办,他还叫我小姑娘。有一天,我对廖公说:“我已是老阿婆了,不是小姑娘了。”他给我写便条,也是小姑娘小姑娘的。我们每星期到廖公家的会客室开一次会,每次开会,先进来的是廖公的爱犬,它一进来,廖公就出现了。廖公进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掏我的口袋,拿一支香烟,点着烟抽上一口,才坐下来开会。廖公有心脏病,医生和家人都不让他抽烟,他就用这种方法时不时抽上一口。
在新华社总社,每逢有同志结婚,廖公总要画一张漫画送给新娘新郎。肖希明和陆冰结婚,他画了一张漫画送给他们。廖盖隆和李蓬茵结婚,他画的漫画,寥寥几笔,就抓住了俩人的特点,两个人的身子却麻花似的扭在一起,谁看了都哈哈大笑。
他这一作风,使很多同志都愿意接近他,但是也有人看不惯。认为这样随便,太不像个领导了。甚至有同志把这一作风和政治水平联系起来。陈克寒同志就曾对人说,廖公政治水平不高。在有些同志看来,当领导的,必须严肃、不苟言笑。否则就没有领导的威严。
1948年新华总社“三查三整”整风,同志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也对领导提意见,对廖公提的意见中有一条是说廖公太爱开玩笑。廖公在作整风总结时,讲完了工作中的问题,最后说:“有人给我提意见,说我太爱开玩笑,我告诉大家,在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讲完一个笑话然后再跳进棺材。”又引得哄堂大笑。
廖公的爱开玩笑,就是在工作之余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他是一个乐天派,他也希望别人快乐。对工作,他是十分认真的。
与华侨、海外同胞以诚相待
建国以后,廖公做侨务工作,他在国外多年,对华侨的甜酸苦辣,了如指掌。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善于和人交往,以诚相见,宽厚相待,这样,华侨和港澳同胞又怎能不把他看作是他们的知心人呢。华侨、港澳同胞来到北京,都愿意见见他,和他谈谈心里话。有的港澳同胞甚至说,到了北京如果没见到廖公,就等于没到北京。因此,廖公对他们的情况、心态和愿望,也就了解得更深刻了。
1960年代,“海外关系”是一个谈虎色变的名词,谁沾上它就有被打入另册的可能。谁沾上“海外关系”,升学、就职,甚至婚姻都要受到影响,而廖公却大声疾呼地反对“海外关系”这种说法。1961年,他说:“这个说法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他说,要说“海外关系”,他最严重,美国过去帮蒋介石训练空军打我们的航空队长陈纳德如果看见他,要叫他舅舅,因为他的妻子陈香梅是他的外甥女。他在香港的亲戚算起来恐怕有四百多人。他就抱着这个“海外关系”大摇大摆地进行国际活动。他不止一次地批驳“海外关系”这种说法。
没有胆没有识,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谁敢这样说!
批准傅聪回国
1979年4月,音乐家傅聪从国外到香港,想回上海参加他父母傅雷和朱梅馥同志平反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是由上海市文联主办的。他必须在两天以内赶到,否则就赶不上这个仪式。傅聪是在他父亲傅雷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吓坏了,不敢回国,从此亡命国外的。香港有关方面的同志把这信息告诉港澳办。我经手此事。我想,音乐家的事应该由文化部管,于是打电话给文化部,文化部的同志说,他是音乐学院的,应由音乐学院管,音乐学院又推给文化部,文化部又由这个局推给那个局,电话来来还还打了无数,谁也不愿点头不愿摇头。时间紧迫,我只得把所有的材料要来,如实给廖公写了一个报告,廖公立马批了,同意傅聪返国。傅聪大概至今不知道,是廖公帮了他的忙。
致蒋经国信传诵一时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公的雄文“致蒋经国信”。这信传诵一时,脍炙人口。信的台头是“经国吾弟”,能和蒋经国称兄道弟的,只有廖公一人。他的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和蒋介石同事,因此,廖公才能在信中同蒋经国话旧,说“幼时同袍,苏京把晤”。信中没有一句套话、空话、废话、训人的话,只是叙旧,问好,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动之以情,劝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信中说:“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接着又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只有廖公有资格写,也只有廖公写得出。我在中山纪念堂遇见一位微雕艺人,他说他要把此信刻在米粒大的一块象牙上。可见此信之深入人心。
电影《少林寺》幕后推手
廖公对文艺有很深的造诣。他常和他母亲何香凝老太太合作画画。在他那间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的会议室里,有一幅很大的何香凝老太太画的松柏图,其中的人物,就是廖公加上的。
他对武打电影,情有独钟。廖梦醒大姐曾告诉我,他们姐弟两人都曾经跟孙中山的保镖马相学过武术,所以他懂得武术,喜爱武术。他看了香港着名武打影星李小龙主演的影片《精武门》后,赞不绝口,还说,这不是一部很好的爱国的影片吗?
他建议香港的电影公司拍两部武术片:少林拳和太极拳。他认为少林拳和太极拳是中国最有名、最厉害的两类武术。香港的一家影片公司写了一个剧本,并已在河南少林寺所在地嵩山开拍。我看到了剧本,觉得不很理想,便把剧本送给廖公。廖公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他说他看了剧本“凉了半截”。他问了影片的导演、演员是哪些人。之后,他说这部片子不能这样拍。他要求修改剧本、调整导演、演员的人选。必要时,可以请日本的导演。日本有一个少林寺联盟,人多势众,而且已对此片买了花(就是已付了买片的定金)。廖公要求找有真功夫的人来演,而决不能打那些花拳绣腿。最后他说我搞过电影,这件事交给我了,要我“搞掂”它。这是广东话,是叫我负完全责任把这件事办好的意思。这下,该我凉了半截了。我说我实在对武术一窍不通。廖公说不懂不要紧,钻进去。他说,据他所知,中国有两个人真正懂少林拳,一位是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一位是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他叫我去找他们,向他们请教。我早听说许世友是从少林寺打出来的,但是他在南京,往返费时,就去找了赵毅敏。赵毅敏同志十分热情,连说带比划,讲了不少。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懂拳术的人,怎么讲得清呢,我仍然不得要领。他叫我伸出一只手来,比划一个招式。当他的手搭在我的手上,我还没有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我的手就痛得哇哇叫起来。这下,我至少领教了少林拳的厉害。
我两次去嵩山,和香港电影界的朋友们研究修改剧本,充实摄制组的人员。李连杰、于海等一批武林高手就是导演张鑫炎物色到的。我每次从嵩山回来,廖公都要详细询问剧本修改和拍摄的情况。他要求服装要唐代的,我说全部重做服装花钱太多,最后只给主要演员重做了服装。我第二次去嵩山,把影片中武打的一些招式拍了录像带回来放给廖公看。
影片拍摄完成后,廖公建议大力宣传。于是,主要演员匆匆忙忙赶往香港,参加影片的首映式,并在电视台表演。影片在春节期间上演,也是根据廖公的建议,因春节看片人多。果然,此片一炮打响。香港电影界都把好片放在春节上映,报纸每天都登载各影院售票情况,影片《少林寺》的票房一直高居第一。此片轰动国内外,港澳人人争看《少林寺》,台湾也有人专门到香港看此片。有人多买到几张《少林寺》的戏票,把戏票作为春节的红包送人,成为最受欢迎的礼物。美国也放映了这部影片。香港各报对该片好评如潮,特别赞赏此片不用替身、不用特技、不用钢丝。这就是廖公所说的不要搞花拳绣腿,要来点真功夫。
这部影片的成功,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以及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努力,固然功不可没,可是真正的“总策划”应该说是廖公。从出题目,一直到影片的“排期”,每一步都是他老人家出的主意。
我曾花了不少时间,拜访太极拳的高手,如北京的吴图南等名家。因种种原因,廖公希望拍的太极拳影片始终没有拍成。我至今觉得内疚。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很好的电视剧《太极宗师》,我想,如果廖公看到,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
|
相关文章推荐:
|
- 上一篇:尼泊尔报纸如何赞颂毛泽东思想
- 下一篇:周恩来和廖仲恺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