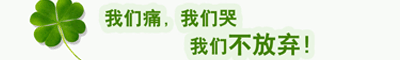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
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呢?像《王子安》、《续黄粱》等描绘升官梦、富贵梦的讽刺小说,显然开《儒林外史》之先河。像《胭脂》、《折狱》那样的公案推理小说,也具有独特的魅力。《快刀》表现刀之快,人头被砍,滚在地上,还喊“好快刀”,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至于意识流,到外国人那里认祖宗也未尝不可,意识流作为派别,作为创作方法,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聊斋志异》中许多描写灵魂离体的作品,如《考城隍》等,不就是中国的意识流吗? 亦真亦幻曲笔传情《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将幻异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和艺术世界。作家对生活采取非现实化的处理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而可采,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换句话说,作家总是将各类精怪的原型性格与人性结合起来,创造出神奇的艺术形象。绿衣女为绿蜂所化,“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葛巾为牡丹花妖,“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阿英为鹦鹉精,故“娇婉善言”。苗生为虎精,故长啸一声,“山谷响应”。所有这些,情趣盎然,让读者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 前人曾言,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确如此。 2.在文体上,蒲松龄创造性地发展了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将魏晋笔记体与史记传记体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小说家的灵活,又有史学家的严谨。作家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论赞传统,在近二百篇作品的结尾,加“异史氏曰”,对所写的人事加以评说,大都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3.《聊斋志异》的语言素来为人称道,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 前人早就指出,读《聊斋》若只当故事看,不做文章看,便是呆汉。甚至说,蒲松龄“有意作文,非徒纪事”,是“才子之笔”。《聊斋志异》的叙述语言简洁、典雅,无论叙事写景,还是抒情状物,无论刻画性格,还是渲染气氛,无不曲折如意,变幻之状,如在眼前。如《花姑子》写安生亲近两个花姑子,一真一假,真的是香獐所化,假的是蛇精所化。真花姑子为安生按摩,“安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安与同衾,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真是美妙温馨之至。当安生与假花姑子(蛇精)亲狎时,“偎傍之际,觉甚腥膻,心疑有异,女抱安颈,遽以舌舐鼻孔,彻脑如刺。急欲逃脱,而身若巨绠之缚。少时,闷然不觉矣。”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尸变》写女尸隔树抓人抱树而僵,本已令人胆寒;作家仿佛还嫌不够味,又写第二天邑宰(县令)到现场质验的情形,“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拳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读至此,更让人心增余悸。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写得同样精彩。这似乎是一个谜。一部文言小说的对话,竟能如出其口,如闻其声,让人叹服。《邵女》篇写媒婆到邵家说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贪图钱财,多少人上门说亲,都不成。媒婆受柴廷宾之托,到邵家说亲,她想以钱说动邵家,却又不好直说,只好拐弯抹角来挑动邵家。 当邵母说邵女反复挑选,一直未定时,媒婆说:“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恶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评论道:”看他于开不得口处开口笑之,驳斥之,无意中以千金动之,末仍以不了语探之,极语言之妙。“这些对话的妙处,就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加以调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语的特色。《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口技》中对各类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模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并不现实,作品中有极少数无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惩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封建观念和文人雅士的风流思想。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邵女》就宣扬妾对妻的无条件服从。作者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对一夫多妻、享受“双美”等丑恶现象也津律乐道,这与现代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那么大的影响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因为要读懂它,首先要过语言关。过这一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聊斋志异》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去突破这一“关”。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被广泛传抄,并受到当时一些名流如王士祯等人的推崇。 之后,抄本、印本层出不穷,说家有其书,未免夸张,但说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却并不过分。有人统计,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聊斋志异》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写本、白话本等,其数量甚至超过《红楼梦》。 |
|
相关文章推荐:
|
- 上一篇:隐姓埋名写尽风情万种——《金瓶梅》
- 下一篇:辛酸泪荒唐言难解苦滋味——《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