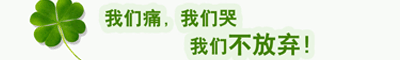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维世从小管我叫“六姨”。维世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请来了当时的着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的一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让我烧掉江青送的照片
建国后,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
|
相关文章推荐:
|
- 上一篇:历史上的薛仁贵的老婆是谁?
- 下一篇:细数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